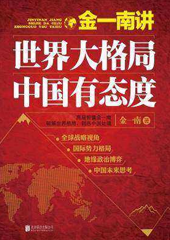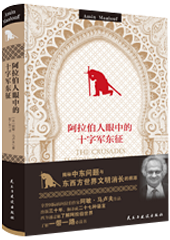我们这一代人是从读毛泽东的书开始起步人生的。读小学时,社会上就“乱”了起来。学校基本没课上,图书馆多贴上封条。除了背诵毛泽东语录和雷打不动的“天天读”外,学校基本就没了其他教育。在这样的大背景中,毛泽东就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启蒙老师。毛泽东的书,我读得早,记得也熟。
入中学后,学校已复了课,图书馆也解禁,但毛泽东对教育的影响还是第一位的。这时毛泽东鼓励大家“认真看书学习”,学历史、学哲学、学马列主义。当时我“响应号召”按当时流传的毛泽东为青年人开的书目,读起书来。先读马列的书,转读范文澜的《中国通史》。范老的文章绝无八股气,极通俗,我从此受益于他的文风──当然,这也是毛泽东在延安倡导的那种文风。那时学校课堂上考勤不严格,更没考大学这回事,我因此有幸脱了如今学生那么大的负担和压力。大量的阅读时间允许我有计划地读了几年书。由此我便结了书缘。
今忆起,觉得当时对我影响毛泽东最深刻,同时也让我最受益的就是毛泽东的书。毛泽东的书使我在人生的启蒙阶段生发了理想和做人的主义;有了理想和主义──尽管当时还很朦胧,就有了做人的根底和方向。我当教师的时候,学生常请我向他们推荐好书,每逢此,我都告诉他们:毛泽东的书会使每个中国青年终身受益。
中学毕业,面临人生的选择。我听毛泽东的话到农村插队锻炼。乡下生活苦,但至今都觉得它是我一生收获最丰的年份。初到农村,我抱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愿,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用仅有的一点积蓄为农民搞科学试验、办夜校,其间有成有败,有快乐也有痛苦。与农民的交往使我知道了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知道了知识人还应向人民学习。四年的苦辣酸甜,特别是其中那迎着刺骨寒风,披星戴月与千百万农民会战黄河大坝的经历,使我知道了中国的农村和农民;知道了农村与农民,从某种意义上说,就了解了中国。现在看来,我们那一代人的下乡经历是今天有些青年人无论如何也理解不出其珍贵的无形财富。正是这一时期的坎坷,使我能够对后来的读书和工作,乃至爱情婚姻中出现的挫折泰然处之;正是这一时期农村生活的天然陶铸,使我养就了朴素的品质,朴素让我的人生过得很充实;最后,还是这四年农村的磨砺,使我了解了国情,这种只有从生活,特别是基层生活学到的知识才使我得以在后来的社会动荡中保持冷静,冷静又使我在无常的生活变化中得以为人无愧,为己无悔,始终保持着做人的本分。
我是考上大学离开农村的,当时毛泽东刚去世不久。随着年纪和阅历的增长,我对毛泽东同志的认识也从感性升华为理性,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从一般的认识论层面深入到更具实践性质的战略层面。这本小册子可以说是这些年我学习毛泽东战略思想完成的学生作业。作业是否及格,这得由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来检验,但这篇作业能够完成,首功当归于中学时每天课前那雷打不动的“天天读”和中学毕业后那几年的下乡经历:前者使我一步到位地接受到了真理性知识——这让我在少年阶段的知识选择中少走了许多弯路,后者使我学到的知识以最直截了当的方式受到实践的检验。有了基层生活经验检验并被证明是正确的知识做基础,我就有了具有扬弃本质的学习能力。这是一种积极的和真正的学习能力,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就能够将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于未来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并由此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
我生逢其时,有幸经历了毛泽东时代。今忆毛泽东在世时的音容笑貌,回味毛泽东的书带给我的有益于我整个人生的教育,总觉得对毛泽东有不尽的谢意和怀念。
这是一篇于20世纪90年代初写的怀念毛泽东的文章,二十多年过去了,文中所思所想,依然如故。今略加改动,代为序
张文木
2016年5月